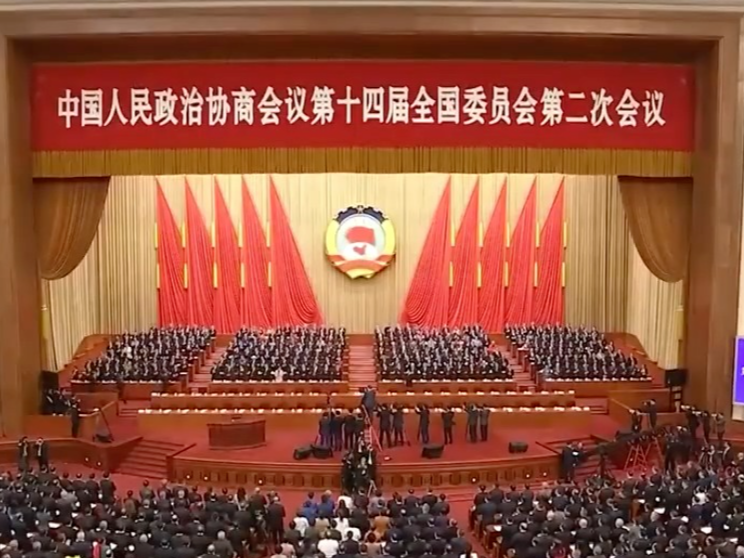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让文物活起来。但是,如何真正有效地做到让文物活起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还是一个有待长期努力的工作,其中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就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种成绩是有阶段性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考古人才奇缺,面对大规模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的需求,1952年北京大学在历史系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山西大学(1978)、郑州大学(1976)等高校陆续创办考古专业。目前高校中开设考古专业的本科院校共有30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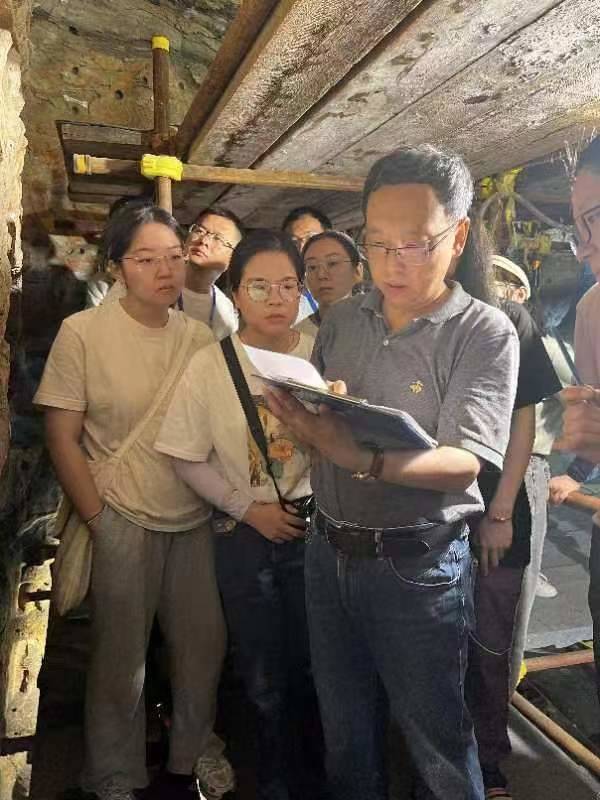
这两个时期以田野发掘为主要内容的考古工作仍然是文物事业的主要内容。随着考古学科的迅速发展,2011年,考古学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种变化一方面意味着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成熟,另一方面也给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问题。除了考古的发掘与研究,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展示阐释、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协调等一系列问题,都并非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点。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文物保护、博物馆等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工作我们做了一些,但因为当时的国力有限,开展得不充分。随着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文化遗产资源被发掘出来之后,如何有效地保护、是否能在更大程度上被公众所认知、能否更好地转换为当代社会教育资源乃至经济发展资源等一系列问题都愈发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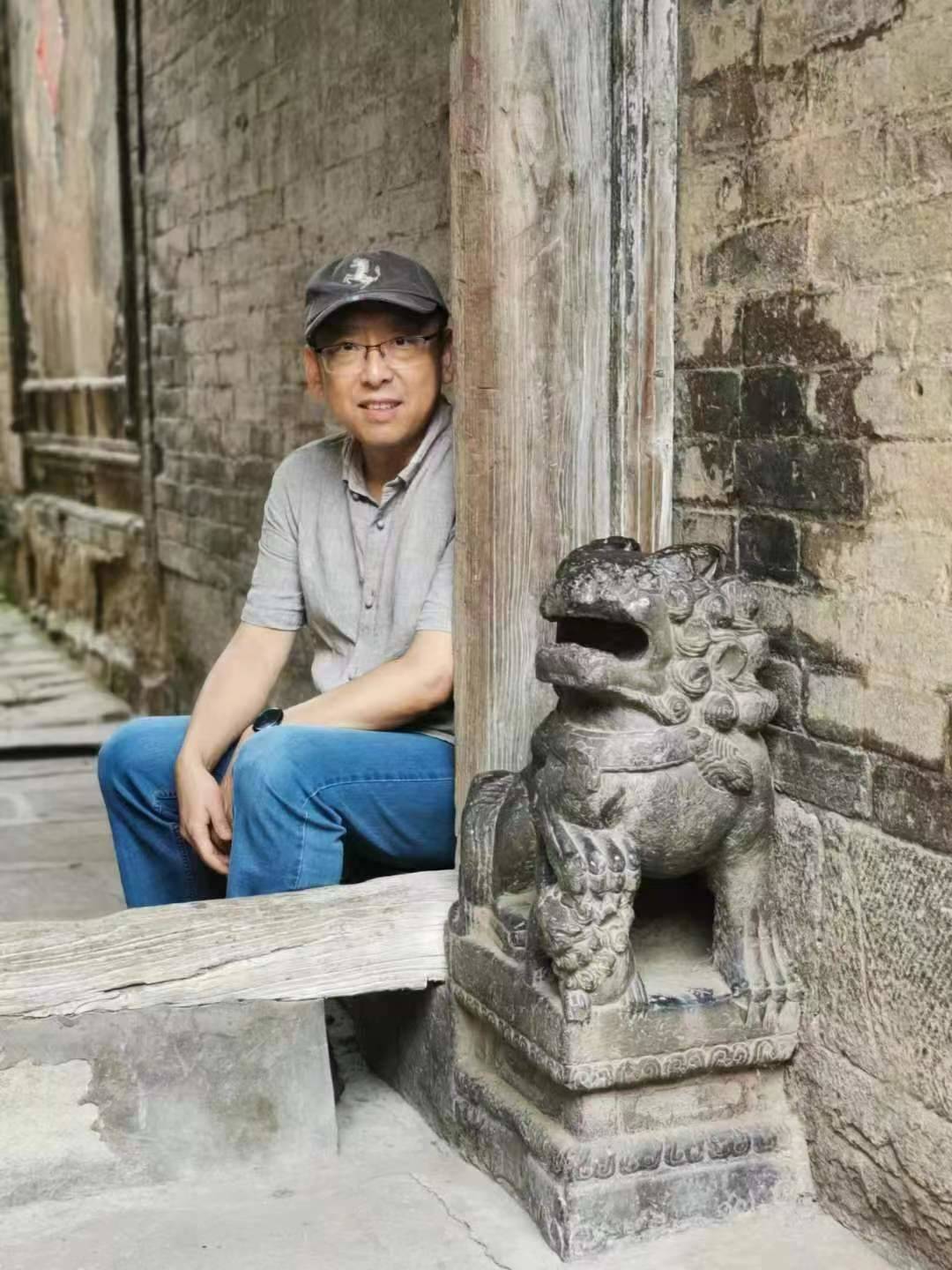
那么这些问题谁来研究?
目前,没有一所学校有文化遗产展示利用的系统的课程设置,举山西大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常说地上文物看山西,我国70%多的元代以前建筑保存在山西,山西大学在1978年开始考古专业招生,也是我国较早设立考古专业的大学,目前有专业教师25名,但是,直到去年底,才引进了一名石窟寺方向的专业教师。2016年至2020年获批立项的2万9千多个国家社科项目中,博物馆学获批10项,占比0.000345;这10个项目中,有7个是从考古学门类中申报。而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我们现在文物系统一年做的展览就有近三万个,一年三万和五年10项相比,博物馆从业者如果能拿到一个博物馆学的国家社科项目,该是何其之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遗产相关学科的理论探讨之不足。
我们的学科发展普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最近的发言中指出,我们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课程始终重解答题目却轻解决问题。我们的理科课程落后世界70年,大量内容是200年以前的知识。这不是个别现象。

考古学为文化遗产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材料,但基础材料要转化成民众能够理解的内容,需要进行转化。《读书》杂志组织过两次“考古围城”的讨论,学者们强调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就谈不上什么“传播”。考古学首先是从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因此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文献史学的概念、术语。作为记录考古发掘材料的考古报告,不要说一般的读者读不懂,就是历史专业的研究者也很难读懂。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这种转换需要有人才作为基础。我们可以想想,《花木兰》、《功夫熊猫》、《中华小当家》、《成龙历险记》等,表现的都是中国题材,但是是外国人拍火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其中很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相关的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

所以,相关的建议是我们在山西重点开展文明起源、三晋文化、民族融合、宗教考古等考古研究的同时,抓住机会,引进教师,系统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与阐释、展示利用的相关课程建设,针对山西的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培养人才,更好地服务山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看大同编辑:杨文迪